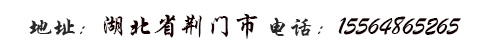偷春
|
治疗白癜风哪家效果最好 https://wapyyk.39.net/bj/zonghe/89ac7.html 春天快过去了吧?空气里已经热烘烘的了,虽然刚下过一场雨,但也无需再添衣,地面、墙壁还有家具表面都蒙上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这个春天哐当一下就过去了。一个多月以前,还筹划着要去公园、植物园什么的,可突然就被禁在家里,无法出门。一天天下来,整个人越来越憋闷,哪怕是站在窗前,听到哪里有猫儿们在打架、求偶,或坐进有绿树环抱的小小院子里,头顶上远的、近的飞落些鸟,或一大早就被催命鬼似的门铃叫醒,跨出门去排起长队做核酸,一路上都晒着暖融融的太阳……春天也似乎竟然与我毫不相干! 幸运的是,某天清早起床,我到外面小院里去取晾干的衣裳,站着,在脱下衣架的时候,竟有一股幽香飘过。我再闻,又没有了,正要进屋,它又来了!那就索性再站一会儿。心里打开了点儿。 香樟 那是香樟树的花开了。这种花腼腆得可爱,香气细微,花朵小如米粒,躲在繁枝茂叶间,很不容易发现,只有一阵风过,才窸窸簌簌地大把大把洒落下来,藏进人工草皮里,扫也扫不走。 说来也怪,我家小院外面的这棵香樟树,就长在垃圾房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间小院与垃圾房只有一树、一墙之隔。周围二十几栋的居民楼所产出的垃圾,都要经由这垃圾房,然后被送出送入每天下午4点半过来的垃圾车里。起初,在来住之前,我还担心着整日要为那酸腐的气味所扰,但结果却出乎意料的没有。哪怕是在疫情封控期间,垃圾车每天仍准时到达,但垃圾房里、房外的垃圾包裹却堆积如山,也丝毫闻不到任何异味。也可想见居民们热闹而繁重的居家生活。 我私自以为,这都是亏了这棵香樟的功劳!站在小院里,并看不到垃圾房,围墙栏杆外只露出半截树干与整个树冠,遮住了小院的一角的天空,越往夏天里走,发枝散叶了,开花了,就越发好看好闻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有载:“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pián)楠豫章。”“章”就是香樟树,“攒荫成巨”,可以长很大。在古代,有一个地方叫“豫章郡”,就是现在的江西南昌市。相传,南昌的松阳县里有一座松阳门,唐朝时,门内有株香樟树,长得十分高大,高七丈五尺(约25米),大二十五围(约8米),“豫章”因此而得名。但“豫”究竟是种什么树?就不得而知了。 除去这棵香樟树,是我大摇大摆、自自在在观赏来的,下面要讲的一些花草树木,就只能算是我“偷”来的了。 我有些任性,还在封控期,就戴了口罩、背起相机溜到家门外。朋友每次都陪我一起。虽然她无心于花花草草,连散步也懒得多走几步,但总乐于帮我解除一些尴尬与责骂。因为这期间屋外无时无刻不有“大白”在“巡逻”,我要是撞见了,一定是只顾埋头逃掉,然而已经被发现,哪里还逃得远,追上了免不了又是一通数落。跟朋友一起,就不用慌了,撞见了,她能泰然自若、慢悠悠地走上去,跟大白聊一两句,他们就神奇地把手一丢,把头一扭,目不斜视地继续往前走去了。我时常站在不远处,观看这一幕,目送大白的背影,暗怀对这位朋友又嫉妒又感激的心情。 二月兰 二月兰有四片紫粉的花瓣,呈长条的菱形,向外展开耷拉下来,将中间小小的鹅黄的花蕊顶出。在宗璞的散文《花的话》里,二月兰被比作成一个谦卑、默默无闻的形象,可在我这里,所望见的二月兰,却是从旁边小区的围栏内,驾着层层叠叠的嫩绿的茎叶,一大丛一大丛地往围栏外涌过来了。虽然单朵的身量的确不及山茶、玫瑰、白玉兰,但我想,它们论的大概不是个。 二月兰又叫萝卜菜,或者诸葛菜。在明张岱的《夜航船》里有载:“诸葛武侯出军,凡所止之处,必种蔓菁,即萝卜菜,蜀人呼为诸葛菜。”为什么要种呢?原来它是可以食用的。至于如何食用,据书中介绍,可生食、可菹(腌制)、可煮汤,还有一定的药效。我没尝过这种菜,但听长辈说过,他们曾拿这种菜喂猪。想起前几周刚看过的一个视频,有一户人家因为物资紧缺,偷采了小区里的绿植来吃,不知道里面有没有二月兰。 棣棠 顺着围栏,转一个弯,走上一条背阴的小路。这里很幽静,哪怕在疫情前,也少有人来。我曾独自躲来这里,坐在沿路草丛的石级上,一边呼吸新鲜的空气,一边在美团上搜寻帮跑腿的外卖小哥。在我旁边,正开着一窝金黄黄的棣棠。花瓣圆胖,呈五星形状,每一瓣与大拇指盖一样大小,不香,但有蜂子在飞上飞下。 琼花(图片来自网络) 几步外的琼花树也开了!奶白的花朵朵团成一团,团得满树都是,但有些还未完全开透,中间星星点点的,还未长大,等再过一段时间,更暖和了,全开成绣球,这棵树怕是兜也要兜不住了吧。 “小姑娘,侬(了)外头做啥事体?”我正举着手机,对着一团琼花要拍,却听见树后的一扇窗户被拉开了,是一位大姐,大约四十岁年纪,把头探出来,盯着我问,末了,又用普通话问了一遍。 我窘了,以为她要举报,但又不好逃走,只得硬着头皮不耐烦地回道:“出来走走啊!” 没想到,她皱起眉头,上半身前倾,好像乞求似的说道:“你可不可以帮我个忙呀?” “嗯?”我一边想着,一边回答她:“怎么了?” “我买的东西,早上就到了,到现在都还没有送过来。”现在已是下午四点左右了,她右手伸出窗外,指指旁边,是一条警戒绳把她所在的那栋居民楼拦在了里面,“我们出不去,家里快没有东西吃了,小姑娘你可以不可帮我去问一问呀?” 我答应了她,立马收掉手机,准备往红棚子那边走。但刚一离开,我又后悔了,要是被大白问起我又是怎么出来的,那不是好心不成还蚀把米吗!算了算了,豁出去了…… 红棚子底下,有一个大白正躺在一张行军床上看手机。见我走来,他瞪大了眼睛,一骨碌从床上翻坐起来。不等他先开口,我就把某某楼栋几零几的一户人家什么时候买的外卖多久到的小区门口等等等等,统统讲给了他。 “这个我管不了。你要不去问问其他人……我们有人会去大门口领取的……你这样去给她说……”这个大白讲得乱七八糟的,我只记得几句,尤其是最后一句。 “我不去!”我生气了,立即逃回了家。 过了几天,我又溜出去了,这一次,我没有再去那棵琼花树下。 我从前面的大路走。大路上大白多,但这一次我却没那么慌了,走到哪儿算哪儿,被抓住了,大不了再折回去呗!但我没有折回去,虽然遇到了好几个大白,他们竟一律装看不见。后来我推想,大概因为那天是中午,太阳又好,刚吃过午饭的吧? 婆婆纳 四季海棠 紫杜鹃 一路上,我拍了许多蓝白的婆婆纳、油亮亮的四季海棠,还有嘈杂得不行的紫杜鹃。杜鹃花是让我感到困惑的。在古诗文里,常将杜鹃鸟与杜鹃花并用,作为一种“愁”的意象。这原是出自一个名叫“杜鹃啼血”的典故,讲的是古蜀国有一位皇帝名叫杜宇,后遭奸人陷害,其灵魂化作一只杜鹃鸟,整日在园中哀嚎,最后咳出血来,染红了近旁的花朵,这花因此而得名“杜鹃”。推想,那被鲜血所染的杜鹃花,应该是红杜鹃吧,并非是这种紫杜鹃。除此之外,我还见过粉杜鹃、白杜鹃、黄杜鹃。之所以让我困惑的是,一来,杜鹃鸟的叫声我是听到过的,“咕咕——咕咕——”,拿腔拿调的,比“啾啾”、“叽叽”低沉,但却圆润,听来并不觉得哀愁;二来,杜鹃花,确切地说是红的杜鹃花,并不跟血的颜色类似,反而像是快没墨的大红水彩笔涂就的,加上其花瓣略显硬朗,如同一个个喇叭,都支楞着,滴滴答答吹个没完,见不到一点哀婉柔情的一面。 但反过来一想,这是不是正是一种“文学比现实更真实”的表现呢?或者说,想象并非虚无,想象就是现实?忘记从哪里得来,《雾都孤儿》出来以前,伦敦早已是烟雾弥漫,但是人们却视而不见,等到这本书一经面世,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原来这里“真的有雾”。不知道这事是不是真的。但想象的力量确实不容忽视,它不仅能催哭古时的李白,一听杜鹃鸣,一见杜鹃红,就发出了“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的哀叹,也能在现在,此时此刻此地,幻化成一头无形的巨兽,横行在大街小巷里,挨家挨户地把我们的生活撕咬成碎片,让许许多多的人感受到了切实而荒唐的痛苦与饥饿。 日本晚樱 还要继续往前走。可是前面已经没有路了,只有一面高高的拉着电网的围墙。越过围墙,是隔壁小区的楼房,楼房外还是围墙。循着围墙,我准备回去。走到另一边的墙角处,能看到立着的一块展览板,旁边晒的有几床不知是哪户人家的花里花哨的棉被。板子与被子同样拼接成了一道墙,只一支粉红的日本晚樱从后面探出了头!原来,这里还藏了一片天地!我撩开棉被,见到三棵挨挨挤挤的粉成一片的樱花树,樱花大朵小朵站在枝子上,好像在极力往外伸展,快要把这里撑破了似的。樱花树底下还有几笼红花继木,几棵大铁树,和围着它们的里三层外三层的山麦冬。我钻进这个粉红的世界里,感到很安心,并同时发现,有一只狗就卧在不远处的墙根底下。它正用一双惊奇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于它,我是个闯入者。但我依然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我们相安无事地保持着距离。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合集#个上一篇下一篇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lasabdf.com/zgnmtl/4653.html
- 上一篇文章: 温州这条秘藏于高山的野花古道,杜鹃漫坡野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